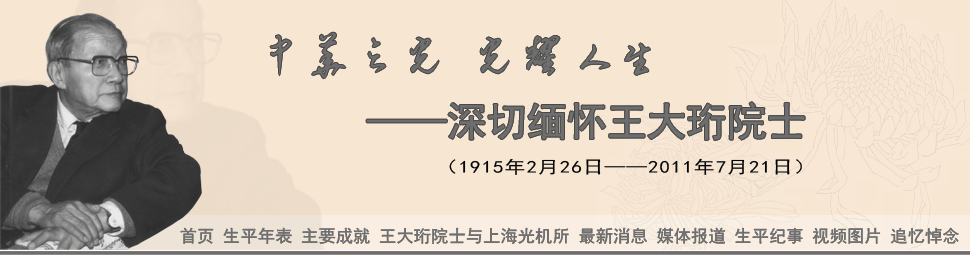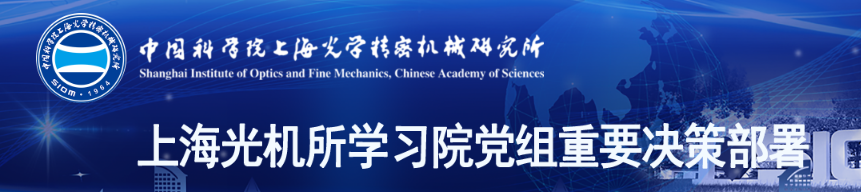三、四个月后,我又退掉了的公寓(王育竹教授也搬到离他单位较近的地方),与一位留学生一起,合租一个民房(我住里间,150,000里拉/每月,他住外间,100,000里拉/每月),陶善昌、宋金安(陕西天文台的访问学者)租在隔壁。这样,这里就成了都灵的“中国城”,大家有说,有笑,相处十分融洽,直到回国为止。
住房解决之后,在吃的方面也要节省开支。我们买东西,除了偶尔去超市购买外,多数还是大家一起到较远的共和国广场去买,那里的东西便宜得多,买得越多就越便宜。中午在单位吃工作午餐,早晚自己烧了吃,既合胃口又省钱。因为我不太会烧,常常将荤菜蔬菜放在一起烧汤,他们开玩笑说:这是单氏烹调法。有时,我还会到其他中国人,如张棕澄那里去吃,他带有固体酱油,红烧小鱼,又好吃,又便宜。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的八大件之梦终于实现了!它为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现在,这八大件已经全部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了。
从国外出国
在CSELT期间,我还先后两次得到ICTP的额外资助,出访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瑞士等国的一些研究所和大学。这些访问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大大地扩大了我的交往范围。
顺便说一下: 在国内,要出国的话,只要领导同意,一切手续都由所里操办,个人比较轻松。但在意大利要再出国的话,在获得了ICTP批准之后,其余手续均需自己办理。如我想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和德国访问或游览,均需我亲自到这些国家驻意大利领事馆办理。一天,我起了个大早,从都灵乘火车到米兰。我差不多化了一个上午,才跑完了这4个国家的领事馆(他们只在上午办公),顺利地拿到了这4个国家的签证。然后,又赶紧乘火车,返回都灵。由于到下午2点还没有吃什么东西,就将随身携带的一罐易拉罐啤酒喝了下去。谁知,人渐渐地感觉不舒服,到达一个公共汽车站时,人就不知不觉地晕了过去。许多等车的意大利乘客,把我扶到旁边的一个长椅上,大约过了一分种的光景,我才慢慢苏醒过来。这些不相识的意大利朋友不断地问我,要不要紧?要不要去医院?因为,我已渐渐恢复常态,就说不要紧,不要去医院,谢谢他们。一会儿,我就乘车回家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在街头晕倒,故而终生难忘。那些不相识的善良的意大利朋友,也将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1986年6月1日,我从都灵出发,乘火车经米兰到维也纳。我在维也纳走马看花似的跑了一天,拍了不少幻灯片。第二天即乘火车赴布拉格。当时,因为我持的是公务护照,在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境时,边防人员还非常客气地向我敬礼致敬,我又一次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6月2日,当我兴高采烈地来到布拉格时,索浩尔教授再一次热情地接待了我,并邀我再次到他家中作客(图6),让我给他的学生介绍中国的激光研究概况,他则资助了我在捷克的全部费用。

图6 第二次到Sochor家作客。
此外,他又一次陪我访问了捷克无线电和电子研究所、物理研究所等单位,与那里的半导体激光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这一次,我住在索浩尔教授为我安排的捷克科学院的招待所里,显得自由自在。在索浩尔教授的陪同下,我尽情地游览了布拉格的大街小巷,特别是老城广场、查尔斯大桥、博物馆、布拉格教堂和布拉格大剧院等著名景点,拍了无数的幻灯片。最令我难忘的是布拉格大剧院里的精彩演出,歌剧演员们先在舞台上唱歌、表演,到了某个特定场景,演员们向后奔去,电影开始。演员们在电影里奔跑的情景与演员在舞台上向后奔跑的情景吻合得十分巧妙,简直是天衣无缝。像这样将歌剧与电影结合在一起的演出,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6月8日,我乘火车离开布拉格,9和10日在慕尼黑畅游街景,拍了不少照片。回国后,我将这些照片给孩子们看。那时恰逢上海电视台搞活动:电视屏幕上展示了不少外国的风景照片,让学生们竞猜,结果我的小儿子单宏寅猜对较多,为此还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让他领奖(半导体收音机)。

图7 与倪国权同志在一起
6月10日,我便乘火车前往瑞士苏黎士,玩了半天,随后前往洛桑。当时,我所倪国权同志正在洛桑的瑞士工学院进修(图7)。出发前,我曾给倪国权同志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到洛桑的车次和时间,请他到车站接我。但这个电话用去我5个瑞士法郎,因为,我打的是投币电话,一般说来,投一个法郎的硬币就可以了,但我手头只有5法郎的硬币。我以为,投币电话是可以找零的,谁知,打完后,等了半天,它也不找零,只好自认倒霉了。
在倪国权同志的帮助下,我不仅在洛桑参观访问了瑞士工学院的实验室和其它许多著名景点,而且,还访问了我向往已久的日内瓦,参观了万国宫。美丽的日内瓦湖以及湖中的喷泉至今还在我眼前晃动。
1986年10月,我又一次得到了ICTP资助,去法国访问了17天,先后访问了巴黎第六大学、阿尔卡特公司、波尔多大学等。10月1日,我从都灵出发,乘火车到里昂。这是一个给人印象十分深刻的城市,整个城市似乎很明显地被分成三部分,十七、八世纪建筑群、十九世纪建筑群、二十世纪建筑群,由北向南,依次排列。游人穿过这三大街区,似乎就走完了几个世纪,真有意思。在里昂,有许多事情难以忘却。一天,我出去游玩,在一个展览馆广场的旁边,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椭圆形建筑,很吸引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厕所,但门是关着的,无法用手打开。我仔细地阅读旁边的说明,然后,将一个1法郎的硬币塞入狭缝,这时门缓缓开启。进去后,里面很干净,还能听到轻松愉快的音乐。出来后,觉得这个厕所很有意思,还专门拍了一张幻灯片,回来让家人猜。那时,我真希望上海也能有这样漂亮的厕所哦。
第二天,我从里昂出发,乘高速火车(TGV)前往巴黎。巴黎火车站的行李车,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行李车很整齐地排成一排,一部紧挨着一部。我走上前去,想取一辆,结果,无论如何也拉不出来。后来,看了旁边的说明,知道要将一个10法郎的硬币塞进狭缝,才可以将行李车拉出来。用完后,将行李车放回原处,这10法郎的硬币还会自动跳出还给你。我试了几次,果真如此。这真是个好办法,难怪巴黎火车站的行李车,虽然无人管理,但仍井井有条。
在巴黎,我住在一位中国留学生那里,我发现,他的住地很小,夜间,我就睡在地板上。虽然,我有ICTP资助,但这种资助是有限的。如果,我能节省开支,肯定会受到ICTP的欢迎。在巴黎,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访问,是访问阿尔卡特公司,访问该公司制作长波长半导体激光器部门,参观他们的检测车间。一般说来,这样的部门,外国人是很难参观到的,但我的意大利朋友托斯柯教授的一个电话,法国人就让我进去了,而且由他们的头头亲自接待,参观后还设便宴招待。

图8与孙洪维一起游阿克松
在巴黎,我还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屋顶,参观了罗浮宫、凯旋门、凡尔赛宫,游览了画市、红磨房等著名街景。一周后,我便离开巴黎,乘火车前往波尔多。当时,我所孙洪维同志(图8)正在波尔多大学进修,在他的帮助下,我参观访问了波尔多大学的一些实验室,并到大西洋边的阿克松游玩。我们赤着脚,在沙滩上行走,尽情地享受着大西洋浪花的抚摸。三天后,我离开波尔多,在图卢兹闲逛了一天,便乘车前往我向往已久的马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我在马赛,只待了二个小时就走了。到马赛后,我一下火车,就觉得不对劲,除了车站的建筑比较新和比较现代化之外,其它的均不如人意。在车站的出口处,有几个妓女站在那儿;车站外面的建筑,比较破旧。我拿着行李向城里走去,一连问了几家旅馆,都说没有空的床位。我继续向前走着,突然,一个年青人,用手拍打着我的右肩,我扭头向我的右后方看去,只见这位皮肤黝黑的年青人,用手势问我,是不是要找睡觉的地方?我说,不!随即回头,这时,另一个皮肤黝黑的年青人已经站在我的前面,并且紧紧地挨着我。我瞪了他一眼,他和后面的那一位,拔腿就跑。这时,我有点慌了,我看了看自己,西装是敞开的,我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东西,发现我的一张全程车票(都灵-里昂-波尔多-图卢兹-马赛-尼斯-摩纳哥-都灵)已被偷去。我又查了一下右面的口袋,发现护照尚在,其它的现金尚在。我定了定神,看看周围,觉得很不对劲,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好象不是法国的马赛,而是阿拉伯或非洲的一个什么地方,房子破旧,人的皮肤黝黑。我开始害怕起来,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于是,我立即返回车站,买好当天到尼斯的车票,当晚到了尼斯。第二天,我游览了迷人的地中海海滨和美丽的都市风景,看喷泉变换多姿,与海鸥拍照嬉戏,我感到十分满足。下午,在回都灵的途中,我还顺访了摩纳哥,在皇宫门前留影,到赌城旁边观光。几个小时后,便起程回都灵,圆满地结束了我17天的法国之行。
善良的意大利人
我在意大利访问期间,曾得到许多意大利人的热情帮助(上面谈到:我在都灵汽车站晕倒时,许多不相识的候车人对我的帮助也是一例),这种帮助使我终身难忘。
在这里,我想真诚地对萨拉姆教授说声谢谢,对弗兰教授、迪纳多教授、托斯柯教授说声谢谢!对在ICTP和CSELT工作的所有意大利朋友说声谢谢!,他们真的十分友好,十分善良,只要有可能,他们都愿意对第三世界科学家提供无私的帮助。
维饶尼(E.Vizzoni)博士与我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只要他发现我有任何需求,都会主动前来帮助。在工作上如此,在生活上也是如此,例如,我想给朋友打个电话,他就会主动拿起电话,先用意大利语请总机帮我把电话接通。有一次,我由于吃了不洁的东西,腹泻不停,一夜拉了16次,最后,连上厕所都感到有困难。好在,王育竹教授与我住在同一个公寓里,不然的话,可真麻烦了。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维饶尼,告诉他我生病了,他立即找了一位医生到我公寓来给我检查。医生将检查结果用意大利语通过电话告诉在CSELT的维饶尼,他再用英语给我解释说:不要紧,肚子不好,吃点药,吃点稀饭,喝点柠檬茶,就会好的。果然,我的病,2天就好了。1986年5月4日,我的意大利同事Calvani还特地邀请我到他那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脚的家中,吃饭、打乒乓,吃得开心,玩得愉快。
这里,我还想特别提一提那位在CSELT负责送信的朋友,他叫Sammaciccia。他对我也特别友好,只要我有信,他总是第一个将信送给我。他说,他曾一个人在瑞士工作过,知道家书值万金的道理。星期天,还常常邀我和另一位中国人(中国科大的陶善昌,他与我一样,由ICTP资助)去他家吃饭。他是天主教徒,吃饭前,要祈祷。他非常真诚,有一次,教会说要支援非洲人民,他真的一天没有吃饭,将这一天省下的钱拿去支援非洲。
我是一个好动的人,在出国期间,常常要利用会议或工作间隙,外出游玩。一次,在的里雅斯特,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周末。星期六,我曾与另外4位中国朋友游览了卢布尔雅那(当时属南斯拉夫,现在是斯洛文尼亚首都)。第二天,他们都觉得累,不愿出去。我决心独自一人从ICTP出发,通过另一个海关前往南斯拉夫的另一个小镇游玩。回来时,想乘的一班从边境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已经开走,下一班车,需等2个小时才能到。从边境到市中心的距离约20多公里,怎么办?我决定独自徒步沿山路返回。我沿公路走了一段时间,突然,一辆小汽车在我旁边停下,我吓了一跳,一位30多岁的先生开窗用英语对我说,我可不可以带你到市中心去?我说,谢谢,你带我到20路车站即可。
我上了车,一开始,心里还有点不踏实,但过不了多久,心就平静下来了,他问我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不乘车回去,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汽车到了20路车站,我下了车,说了声谢谢,他就将车开走了。现在,想起来,我真后悔,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问,就这样让人家走了。此事留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将他看成是意大利的雷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这位普通的、善良的意大利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1985年3月,我第一次访问都灵。头一天,我已乘过62路,到CSELT门口下车。第二天,我还要去。于是,我仍在车站乘上62路。谁知,这个62路在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我就发现,线路与昨天的有所不同。我从口袋里拿出写有CSELT地址的纸条,交给司机。他一看,便摇头,用意大利语说我乘错了。我说,这不是62路吗?他和许多乘客,都一再向我解释,这是62路,但不到CSELT。后来,司机停下车,将我送到从马路对面开来的62路车上,并用意大利语给对方交代了什么,才回来将他的车开走。从对面开来的车,开了一阵之后就停了下来,又亲自下车将我送到马路对面的62路车站。这时,我才发现,在这个车站,有两块62路车牌,一个就是62路,另一个在62上有一个斜杠。这位司机特别指出,要我乘没有斜杠的62路,他确信我弄明白之后,才回到马路对面,将他的车开走。过了一会儿,没有斜杠的62路来了,我上了车,顺利到达目的地。到了CSELT之后,朋友给我解释:62路公共汽车有2条路线,一个终点是相同的,另一个终点不同。从我的旅馆到CSELT,应该乘没有斜杠的62路,而不是有斜杠的62路。这件事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觉得:都灵的公共汽车司机实在令人可敬!为了帮助我解决难题,他们能特地将正常行驶的车停下来,亲自将我送到对面的车上,这样的司机心地是何等善良啊!
在意大利期间,我也碰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如贫富差别太大,就是其中之一。我所在的单位,CSELT是1964年成立的,到1983年,人员达661人,年投资水平达200多万美元。里面设备先进,办公场地宽敞,人与人之间亲密融洽。我上班时,从大门口到办公室,这一路上,不断有人给我打招呼、问好。但是,在离CSELT大约300米左右的地方,就有一个吉普赛人的营地。这些吉普赛人住在破旧的汽车上,共用一个在营地门口的自来水龙头。这两个群体,真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一次,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自行车丢了。他确信,是隔壁的吉普赛人拿的,但是,他不敢只身前往吉普赛人营地。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爬上CSELT的一个100多米高的通信塔顶,用望远镜在吉普赛营地搜索。果然,他发现:他的自行车确实在吉普赛营地里面。他高兴极了,打电话到警察局,在警察的陪同下,到吉普赛营地将自行车领回。